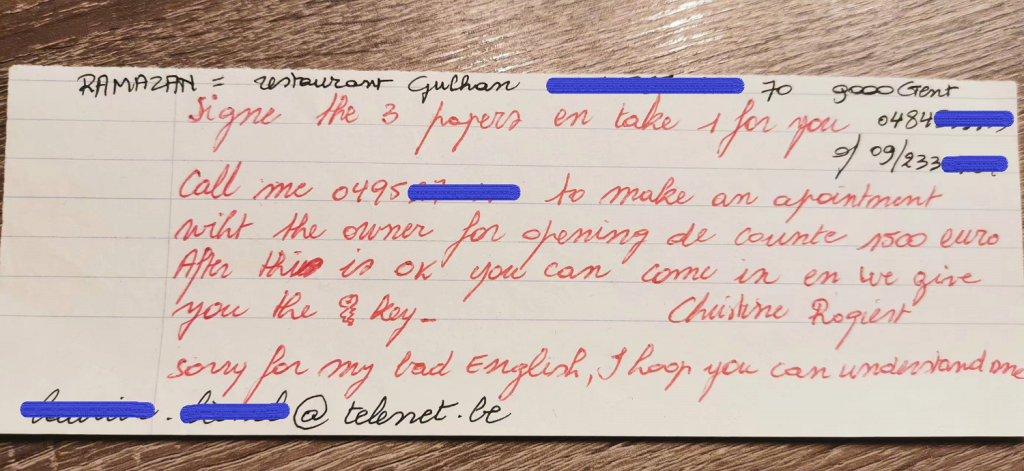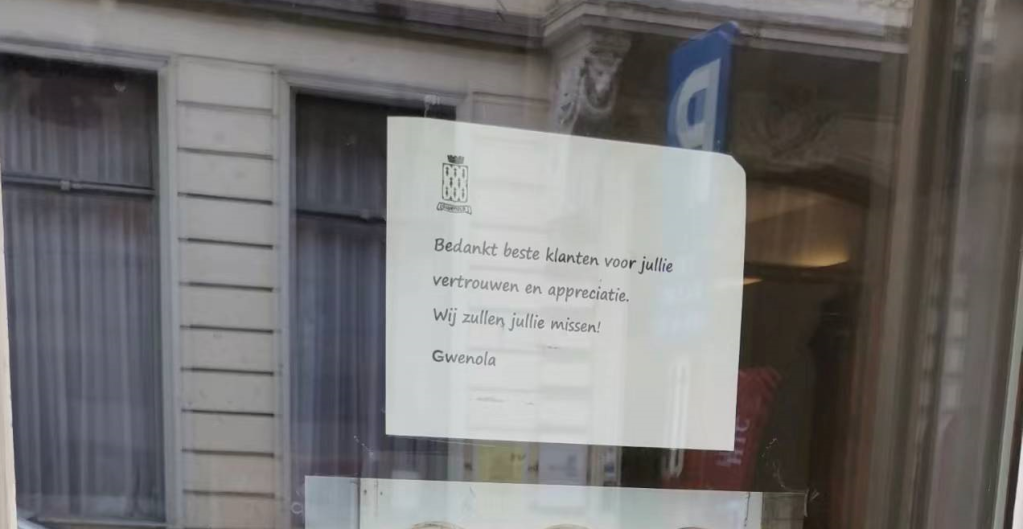今天有朋友发了个圈,用了陆游的两句诗:故人不见暮云合,客子欲归春水生。这几年瘴疠连绵,刀兵不绝,凛冬已至,故土难归。看罢,未免心有戚戚焉。
故乡有一个小镇叫“暮云市”,它位于长沙和湘潭之间,是京广线和107国道的交汇点之一。小时候我随母亲经常坐湘运的大客车从湘潭去往长沙,每当看到铁道出现在窗外,用不了多久客车便会顺路拐上跨线桥,下桥后又重新扭头向北,便知道要到暮云市了。
暮云市虽然叫做“市”,却只是一个小镇。从小到大我往返长潭两地应该不下百余次,经过此镇也有百余次,却从未下车停留。之所以对这个镇子印象如此之深,只是因为它的名字太美——听到“暮云市”这三个字,脑海里就是一幅晚霞低垂、酒旗漫卷的黄昏景象,这个意境岂是“大托铺”、“板塘铺”等地名可比?
关于暮云市这个名字的具体出处,并没有一个定论。可能是因为古诗词里关于“暮云”的描写实在太丰富了,以至于可以附会的太多,最后竟然无从附会。不说其他诗人,就说陆放翁,除了朋友发的这首《登剑南西川门感怀》,他还有“多情谁似南山月,特地暮云开”,还有“暮云如泼墨,春雪不成花”,还有“细细香尘暗六街,鱼鳞浅碧暮云开”……他简直太爱这漫天晚霞了!
而在其他诗人的篇章里,“暮云”也比比皆是。如李白的“城隅渌水明秋日,海上青山隔暮云”,如杜甫的“渭北春天树,江东日暮云”,如白居易的“野绿全经朝雨洗,林红半被暮云烧”,如李清照的“落日熔金,暮云合璧,人在何处?”,如纳兰性德的“凭高目断征途,暮云千里平芜”。若说朝云是苏子的专爱,那暮云简直是诗人们的“团宠”了。
清光绪《湘潭县志》记载,“自涓口发舟,便已遥见阴云接暖,百里所瞻,或题其阳为朝霞,阴为暮云”。涓口,指的是涓水汇入湘江的地点,位置在现在易俗河附近,离暮云市尚有几十里的距离。从涓口驾一叶扁舟出发,不多久就远远看到云蒸霞蔚,乌云彩霞相连百里可见,其霞光灿烂者为朝霞,阴云低沉者为暮云。可见“暮云”二字,大多情形下指的是较为厚重的云彩,自带深沉、肃杀、萧然的意境,最适合去国怀乡、感极而悲者。
清代“同光十子”之一的刘善泽,在《暮云市》一诗中写道:
疏疏墟落暮云村,江岸人归日近昏。
萧瑟平林鸦数点,西风残照是秋痕。
秋末江边萧瑟、凄冷的景象透出纸面。
不过,在我所有的儿时记忆中,暮云市总是美好的。
小时候去长沙,常常是去和父亲团聚,返湘潭,往往是回到外公外婆家。父亲当年在长沙工作,带着妹妹在身边,母亲在湘潭河东一所中学教书,而我被寄养在湘潭河西的外公外婆家。一家四口分居三地,日子聚少离多,难得碰到假期,便想着能够团聚几天。
不论是从湘潭去往长沙,还是从长沙回到湘潭,车至暮云市,就意味着行程只剩下一半了。车过暮云市,时间就会变快不少。座椅伴随着车体的晃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,和着满车的乡音,简直要成为一曲欢快的交响乐,连同窗外的景象都变得越来越亲切,即便是国道旁那些“补胎打气”、“水煮活鱼”的招牌,也变得越来越生动了起来。
父亲和妹妹临时的家,被安置在一个实验楼中。这栋两层的实验楼位于天马山下的一块空地上,远离大学的中心,围墙外就是校办工厂和郊区农田。系里领导体恤单身爸爸的不容易,在实验楼中撇出两间实验室来,算是给父亲安排了一个落脚之地。我们当时年龄小,只是觉得这独门独户自由自在,夏天抓些萤火虫,冬天敲几块冰溜子,那是有多么惬意!
想必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在实验楼外面开出了几小块地,种上了青菜、辣椒、苋菜、豌豆,撒上些青葱、绿蒜、香菜、紫苏,再喂上两只鸡,把日子过得满满的。开春后天气暖和起来,菜苔一天能往上窜一大截,同事们下班顺便带上些,就不用再去菜场了。
要是母亲和我从湘潭过来,父亲一定会起个早,摸着黑骑车去菜市场排队,买些好鱼好肉回来。新鲜的草鱼只需经过简单的处理,抹上一些细盐,在锅中煎到两面微黄,再加入生姜蒜瓣青椒,倒入开水,盖上锅盖美美地煮上十来分钟,简单调味后最后加入一把紫苏叶,这锅水煮活鱼也就有了灵魂。
当时已是半大小子的我,和妹妹一样都非常爱吃鱼。每每父亲把鱼端上来,用不了几分钟桌上就已经是一副风卷残云的景象。父亲和母亲只是笑笑,说:要是有客人来,你们可不能这个样子,要记住哦。
又过了几年,母亲被调到岳麓山下,我们一家终得以团聚。再过一年,我们搬离了实验室,住进了五十年代落成的教师新村。这套房子虽不大,但五脏俱全,加上厕所大大小小一共五间房,一字儿排开,像极了一列火车。
外公外婆早已退休,他们会拣暑假后天气转凉的时节来长沙小住。当时电话尚未普及,两地联络主要靠写信,那一头外公外婆在信中告知半个月后的行程,这一头收到信的我们在那一天便会早早地在门前的坡上等候。
外公怕热,夏日里常常穿一件老头汗衫,一把蒲扇不离手。外公说,立秋后还有二十四只秋老虎呢;我们不知道这个说法的具体来源,但秋老虎们确实往往被他言中。外婆的穿着要讲究、精致得多,一头银发梳理得清清爽爽,穿一身绵绸的衣裤,她步子虽然不快,但走起来总是带着风。
外公的行李只是一个帆布包,里面除了换洗衣服,就是厚厚的几本书了。外公读的书很杂,除了他喜欢的人文词话、书法国画以外,还有不少诸子百家和趣闻野史。也许是白天太热的缘故,外公习惯于晚睡晚起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正是他读书的好辰光;有时候我们一觉醒来,外公所在的“卧铺车厢”仍然有依稀的灯光透出来。
外婆的生活则要健康、有规律一些。在岳麓山小住的日子里,外婆总是早早起床,换上一双轻便的鞋,挎上那把父亲给她买的太极剑,赶在暑气升起来之前去山脚下晨练。等她舞了两套剑,走了一大圈回来,正好是我们准备吃早饭的时间。有一次,外婆告诉我们:今天碰到几个新来锻炼的中年人,说我动作蛮标准的,还问我是哪个系退休的老教授呢!看到外婆开心的样子,我心里一乐:哈哈,谁能想到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现在还在床上酣睡呢?
再过了一些年,我离开长沙去外地求学,外公外婆的年纪也越来越大,来长沙小住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慢慢地,书和剑都留在了老家的橱柜之中。
前些年,外公、外婆和父亲相继过世,母亲和妹妹在上海生活。暮云市这个小站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路过,它就像一滴溅洒在桌布上的美酒,香气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散去,变成了一块暗红的酒渍。
这几天,村里已经开始入冬,暮云低垂,冬意凛然。今天我从朋友圈看到陆游的这两句诗,便想起了家乡的暮云市,便隐约看到父亲给我们兄妹俩端上有了灵魂的水煮鱼,仿佛看到外公穿着老头汗衫、背着电业局的帆布包,摇着一把蒲扇笑盈盈地从坡下走上来。
心里,便是暖暖的。